Spreading characteristic and purification effect of air pollutants in passenger cabin of a high-speed train
-
摘要: 高速列车客室环境相对封闭,列车运行时,在送风方式和客室结构的综合影响下,空气污染物在流场中的传播特征复杂多变。本文基于具有完整空调系统、客室内装和风道结构的高速列车客室流场开展实车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客室中部产生的固态污染颗粒会造成上中下游污染物浓度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下游的污染物浓度上升最为剧烈。顶部送风模式相比于底部送风模式能够更好地抑制污染物在客室空间内的传播。最后,以静电除尘技术和介质阻挡放电技术为代表的空气净化技术能够显著提升客室空气污染物的净化效率,二者的空气净化效率和客室空气污染物浓度呈正相关,且静电除尘技术的空气净化效率优于介质阻挡放电技术。Abstract: The passenger cabin of a high-speed train is relatively well-sealed. Thus the spreading characteristic of air pollutants within the cabin may vary significantly under operation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ventilation modes as well as the cabin layout structure. The present work conducted a systematic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air pollutant spreading characteristic in the passenger cabin of a real high-speed train with a complete air condition system, wind passage structures and cabin decor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ir pollutants emerged in the middle of the passenger cabin can spread to both ends of the cabin,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e of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to different level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Particularly, the downstream can reach the highest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The top air supply mode works better in restricting the air pollutant spreading than the bottom air supply mode. Two air purification techniques, i.e., intense field dielectric (IFD) and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DBD),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urification effect of air pollutan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air purifica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ir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Moreover, the IFD technique exhibits a better purification efficiency than that of the DBD technique.
-
0. 引 言
高速列车的舒适性和安全性是我国轨道交通领域发展的一个永恒话题。目前,关于列车客室环境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流场温湿度和速度指标下的乘客舒适性研究,对于列车客室污染物空间扩散规律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表明,客室内的小粒径固态污染物(如PM2.5、PM10等)浓度通常是室外环境的2~5倍,极端情况下可以高达100倍[1]。在高浓度可吸入颗粒物暴露的环境下,人体的患病和死亡风险都会显著增加[2-4]。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固态和液态悬浮颗粒为代表的空气污染物在封闭空间内的传播特性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5]。对于高速列车而言,明确污染物在客室内的动态传播规律、空间分布以及典型净化技术对污染物传播的抑制效果,对列车客室空气污染物的抑控、净化以及客室空调系统风道结构和送风参数的优化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目前,针对载运工具客室污染物传播模型的研究主要分为数值模拟研究和实验研究两类。在数值模拟研究方面,针对载运工具客室的湍流流动环境,先后有不同学者基于各类瞬态湍流模型(雷诺时均模型、分离涡模型、大涡模拟等)针对载运工具客室环境开展了系统性计算流体力学数值仿真研究[6-8]。此外,一些学者在流场特性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流场中液态[9]、固态[10]污染物在客室空气中的扩散机制。虽然数值模拟研究相比于实验研究具有更高的计算效率,但是其对于边界条件、计算域和几何结构均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简化,其计算结果与真实情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为了验证数值模拟研究方法的准确性,同时真实反应包括风道系统、客室内装和标准送风模式下的客室环境流场特征,多位学者相继针对飞机、汽车等代表性载运工具的客室环境流场结构和温湿度等参数进行了实验研究[11-12]。然而,针对高速列车客室内流场环境的研究,尤其是固态、液态污染物在客室环境中的扩散传播过程的实验研究目前为止还较为匮乏。现有研究大多围绕客室的温湿度和压力舒适性的内流场实验展开[13],无法为污染物在客室内的传播特征提供直接借鉴。
对于空气环境中的污染物扩散这一问题,已经有多名学者从医学和工程等多个研究领域开展了系统性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大多数致病污染物主要以液态气溶胶颗粒的形式悬浮在空气中[14],但是如果为了实现对于污染物颗粒统计学传播特征的全面动态捕捉,不论当前的数值模拟研究技术或者是实验技术均无法满足上述需求。Luca学者从数值模拟角度证明,室内流场中的小粒径固态颗粒(如PM2.5,PM10)和液态颗粒的动力学传播特征差异并不明显。因此,可以通过对固态污染物颗粒的释放、追踪和检测,实现对客室空气污染物动态传播特征的归纳和概括[15]。
在高铁客室污染物净化研究方面,现役列车常见的净化方式为G1或G2级滤网净化,该滤网对空调系统混合腔内由新风和回风组成的混合空气进行过滤处理,能实现对一定粒径以上的固态、液态颗粒的净化[16-18]。然而,上述滤网只能实现对不同粒径固态污染颗粒物的拦截,而无法针对污染颗粒物内的有害成分实现净化。为了实现对运行状态下高速列车客室污染物的持续清洁,可以借鉴现有的针对建筑环境内空气净化的基于介质阻挡放电技术(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 DBD)[19]和静电除尘技术(intense field dielectric, IFD)[20]等高效环保的灭菌除尘方式。
鉴于上述现状,本研究基于具有完整空调功能、风道结构和客室内装结构的某型高速列车实验平台,通过播撒浓度、速度可控的固态污染物颗粒发生装置模拟污染物的产生过程,利用实时监测设备对客室污染物浓度进行记录,实现对典型高速列车客室通风模式下污染物在客室空间内传播过程的捕捉。在此基础上,检验基于静电除尘技术和介质阻挡放电技术的两种代表性空气净化方案对客室污染物的净化效果。研究成果能够揭示典型客室流动环境对污染物动态传播过程的影响机制,明确污染源对客室不同代表性位置的影响程度,为后续的实验研究提供技术方法借鉴,为高速列车客室数值模拟研究提供实验数据验证支撑。
1. 实验设置
1.1 实验环境
本实验基于具有完整内部装饰、风道系统和全部空调功能的某型高速列车客室。该客室的风道结构对应的进出风方式为分散式送风、集中回风的通风结构,新风口位于新风/回风混合腔的两个侧面,回风口位于混合腔的底面,呈对称分布。客室共有13排座椅,每排5个座位,呈3+2模式分布,如图1所示。污染源由颗粒污染物发生器进行释放,释放的初始流量为0.004 m3/s,初始方向为图1中x方向的正向。释放的固态污染物粒径范围在1~100 μm之间。释放位置在客室流场的中游(如图1所示),以此代表列车中部过道位置附近乘客释放的污染物的扩散范围。经测量(CLIMOMATER6501),污染源在发生位置附近的温度为36°左右。考虑到污染源的释放速率和列车客室流场的空气体积,本研究不考虑污染源对客室流场温度的影响。此外,除了现役高速列车中常见的G2等级滤网之外,本研究还在客室内装天花板的4个代表性位置以及车内空调系统的新风/回风混合腔内(A区域)的两个代表性位置安装了基于介质阻挡放电技术的小型净化设备。并且在空调的混合腔内加装了可控制开启的基于静电除尘技术的空气净化滤网。客室结构和净化装置如图2所示。
![]() 图 2 净化装置和客室结构布置图:(a)污染物发生装置;(b)介质阻挡放电装置代表性安装位置(图片左上方);(c)静电除尘装置安装位置(图中左侧滤网附近位置)Figure 2. Air purification unit and passenger cabin structure: (a) air pollutants generator; (b) typical installation location of the DBD unit (upper left of the picture); (c) installation location of the IFD unit (near the filter on the left of the picture)
图 2 净化装置和客室结构布置图:(a)污染物发生装置;(b)介质阻挡放电装置代表性安装位置(图片左上方);(c)静电除尘装置安装位置(图中左侧滤网附近位置)Figure 2. Air purification unit and passenger cabin structure: (a) air pollutants generator; (b) typical installation location of the DBD unit (upper left of the picture); (c) installation location of the IFD unit (near the filter on the left of the picture)1.2 实验设备
基于客室的风道回风结构,在空调系统正常运行时,客室内部会形成一个沿过道方向的纵向气流。为了全面反映污染物在客室流场中的动态传播过程,本研究选择了上游、中游、下游三个测点,针对空气污染物的浓度进行监测,监测指标为PM2.5,即粒径在2.5 μm 及以下的总悬浮颗粒浓度。基于本研究的特殊需求,本实验采用的测量设备为项目组自行研发的高频污染物浓度检测设备,目前有三台工程样机进行持续、准确监测,因此本实验只能针对三个代表性测点进行测量研究。污染物浓度监控传感器具体参数如表1所示。
表 1 污染物浓度传感器性能参数Table 1.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the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sensor检测原理 检测量程 PM2.5检测精度 数据采集频率 激光散射
原理0~1000 μg/m3 ≤100 μg/m3; ±10 μg/m3
100~1000 μg/m3; ±10%
(以GRIMN作为参考,
25±2℃,50±10%RH环境条件)1 Hz 1.3 实验方法
实验过程中,三台监测设备均处于记录状态。本研究将污染源视为一个固定位置的点源,以此模拟列车中部过道位置附近乘客释放的污染物。在每轮实验开始前,首先使客室空调持续工作10 min,然后进行污染物颗粒的释放,释放时间为10 min。污染物释放完毕后,通过监测设备持续记录客室内污染物浓度的示数20 min,即为一轮实验。此外,在实验全程中,列车客室的所有车门处于封闭状态,即客室与外部环境的新风交换完全通过空调系统进行。上述实验条件与实际运行时的列车条件一致。
2. 结果与讨论
为了提取污染物在高铁客室中的典型扩散特征,本研究基于客室空调系统的送风模式,针对内循环模式、外循环模式、顶部送风模式、底部送风模式,以及加装空气净化设备之后的送风模式等几类关键参数综合作用下的工作模式,梳理了8种典型工况进行对比分析。
由于列车客室送风系统是多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本研究针对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组合共选取了八种代表性工况,在结果讨论分析中以工况1至工况8进行表示,每个工况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
表 2 研究工况Table 2. Cases under investigation工况编号 送风/空气净化技术条件 1 内循环-底风-G2滤网 2 内循环-底风-G2滤网 + DBD 3 内循环-底风-G2滤网 + IFD 4 内循环-顶风-G2滤网 5 内循环-顶风-G2滤网 + DBD 6 内循环-顶风-G2滤网 + IFD 7 外循环-底风-G2滤网 8 外循环-顶风-G2滤网 2.1 送风模式对污染物空间扩散规律的影响机制
基于客室的风道结构,通过热线风速仪(CLIMOMATER6501)的测量结果表明,在客室的纵向方向(图1中x方向)上会形成一个平均速度为0.6 m/s左右的纵向气流。而污染源的产生位置又介于上游测点和中游测点之间。因此,本研究首先对空气净化装置关闭状态下的四种代表性工况(工况1、工况4、工况7、工况8)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所有空调运行状态下的典型工况均会造成污染颗粒物在上中下游的全场分布。为了进一步分析污染物颗粒的动态演化规律,选取上述四种工况的实验过程中污染物峰值浓度最高的工况(工况1)下不同测点位置污染浓度(PM2.5)的时程变化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见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出,实验最初十分钟,即污染物发生装置开启之前,客室的颗粒物浓度呈现小幅下降趋势,这是由于安装在空调系统中的G2滤网对空气起到了一定的净化作用。在污染物发生装置开启之后,中游测点由于受到列车客室内纵向流动的影响,其污染物浓度上升的速度明显高于其余两个测点,且PM2.5峰值浓度也高于次高的下游测点24.18 %。此外,下游测点的污染物浓度上升速度也明显高于上游测点,其峰值浓度高于上游测点17.87%。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研究通过热线风速仪对客室环境中的流速和流向的测试发现环境中存在0.6 m/s左右的持续纵向流动。但是图3中的实验结果表明,分布在上游测点和中游测点之间的污染物颗粒发生器产生的污染物同样能造成上游测点污染物浓度的显著提升。这种现象是由于客室内装结构和送风风道、回风风道和废排风道的导致的局部湍流效应造成了空气对流效应下空气污染物颗粒从下游向上游方向的传递。
从图3中还可以看出,在污染物的初始播撒过程中(即开始播撒后的3~5 min内),车厢内所有测点的PM2.5浓度均会产生较快的上升。在播撒开始5 min之后,客室PM2.5浓度的增长速度显著放缓,并且呈现一定的波动趋势。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1)污染物发生装置的产生速率是恒定的,在污染物释放一定时间之后客室内的污染物浓度会在空调通风系统的作用下逐渐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在此过程中浓度的增速会逐渐放缓。2)客室的空调系统会依据设定的温度和室内温度调整压缩机的工作状态,当压缩机打开或关闭时会造成送风系统风量在一定范围的波动,从而对客室内的流场稳定性产生一定的扰动。上述现象是造成图3中中游测点污染物浓度在实验阶段第14 min至第20 min波动的原因。除上述影响因素之外,从图3中还可以看出,当污染物释放停止之后,客室内所有测点位置的污染物浓度均显著下降,并且浓度高的测点位置污染物浓度下降更为迅速。在实验的第24 min,上中下游的三个测点污染物浓度基本上下降到同一数值水平(200 μg/m3),并自此之后保持基本一致的速率持续下降,直到实验时间结束。上述实验结果表明,当污染源停止播撒时,客室内装和送风结构导致的对流效应能够在 5 min左右的时间内实现污染物在客室过道上中下游的均匀分布,而这种均布也不会受到客室中持续纵向流动的影响。
基于不同工况下所有测点污染物颗粒浓度的峰值数据分析结果,污染物颗粒的浓度峰值均出现在中游测点。为了更加详细地展现客室污染物浓度的动态变化,图4呈现出了在4个标准工况下客室中游测点污染物浓度的变化情况。表3基于上述典型送风工况,列出了在每种工况下空气污染物颗粒浓度的峰值及其对应时间。
表 3 典型工况下污染物颗粒浓度峰值及达峰时刻Table 3. Peak concentration and the time to peak of pollutant particle concentration for typical cases送风模式 PM2.5浓度峰值/(μg·m–3) 达峰时刻/min 工况1 344 19 工况4 275 15 工况7 294 16 工况8 262 15 从表3 中可以看出,内循环、底部送风模式下的污染物浓度最高,其次是外循环、底部送风模式,而外循环顶部送风模式的污染物峰值浓度最低。上述结果表明,在内循环模式下,顶部送风模式更容易抑制污染物的传播扩散,其污染物浓度峰值比底部送风下降了20.06%。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出,外循环模式相比内循环模式能够显著地降低客室污染物浓度的峰值,且具有更高的净化效率。本研究的实验中所使用的外循环工况为62.5%回风、37.5%新风,相比于100%回风的内循环工况,在顶部送风模式下能够降低污染物峰值浓度4.73%,在底部送风模式下能够降低客室污染物峰值浓度的14.53%。然而,考虑到本实验的污染物播撒设置在实验的第20 min截止,上述结果表明底部送风模式下,在10 min的播撒时间内,本实验所采用的播撒设置参数并没有与客室的通风系统实现一个平衡的状态,且随着污染物颗粒浓度的升高,中游测点的污染物浓度波动更为剧烈。上述结果表明,在客室污染物颗粒浓度较高时,污染物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会相较于低污染物浓度情况下显著增强,并且底部送风造成的湍流脉动和污染物浓度的时空波动相较于顶部送风更为剧烈。
此外,在客室污染物播撒停止之后,客室环境中的污染物浓度仍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此时,客室污染物的浓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下降,以每种工况下PM2.5浓度从160 μg/m3降低到80 μg/m3所需时间作为净化效率参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上述浓度区间内,外循环模式对PM2.5的净化效率比内循环模式高4.68%,底部送风模式对PM2.5浓度的净化效率比顶部送风模式高5.76%。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底部送风模式下创造了更加明显的沿客室底部向顶部送风的气流,由此一来客室顶部的回风口能够收集到更多的污染物颗粒,从而通过装在新风、回风混合腔内的滤网实现污染物颗粒的净化。
鉴于现有列车上已经装配有滤网装置,该装置能够通过物理过滤的方法,实现对空气中固态污染颗粒物的拦截和净化。因此,图4中的四种工况下污染物浓度平稳下降的区域,即客室污染物浓度从160 μg/m3降低到80 μg/m3(污染物浓度减半)过程的时间,展示于表4中,从而比较不同送风模式下空调系统混合腔中G2级滤网对污染物的净化效率。结果表明,不同送风模式对于G2级滤网的污染净化效果影响有限,除了内循环、顶部送风模式下滤网的净化效果在12ʹ20ʺ左右,其余三种工况的污染物浓度下降时间均在11ʹ09ʺ至11ʹ30ʺ之间,差异并不明显。
表 4 PM2.5浓度从160 μg/m3降低到80 μg/m3所需时间Table 4. Time required for PM2.5 concentration to decrease from 160 μg/m3 to 80 μg/m3工况 时间 工况1 11ʹ20ʺ 工况4 12ʹ20ʺ 工况7 11ʹ09ʺ 工况8 11ʹ27ʺ 2.2 空气净化技术对污染物空间扩散规律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选取了两种典型的空气净化技术的工程化装置,并在高铁列车客室内进行了安装(如图1所示)。为了排除外循环模式下外界环境污染物浓度变化对不同净化技术净化效率的影响,本研究全部选取内循环工况对净化技术的净化效率进行测试。两种空气净化技术的基本原理如下:
2.2.1 静电除尘技术
基于静电除尘技术的工程装置原理如下:首先,将空气送入电介质材料内的众多空气流动微通道中。此时,电介质材料包裹的电极片会在微通道内产生一个高压电场。在电场的作用下,流经微通道的空气污染物粒子会在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下吸附在材料表面。通过上述方式,不仅能够实现对于空气中固态污染颗粒物的高效过滤,还能在电场的作用下有效杀灭依附于固态污染颗粒物表面的细菌和病毒等微生物。本研究将基于静电除尘技术的空气过滤装置安装于高速列车的空调机组送风口处,经实验测试表明,增加了静电除尘技术的过滤模块将空调系统的沿程阻力提升了30 Pa左右,属于空调系统运行过程中可以接受的范围。
2.2.2 介质阻挡放电技术
基于介质阻挡放电技术的空气净化技术主要依靠电场对空气的电离,并依靠空气中产生的正离子、负离子实现对空气污染物的净化。上述技术尤其对以细菌和病毒为代表的污染物成分具有显著的净化效果。本研究共使用了6个基于介质阻挡放电技术的装置,其中两个装置安装于空调混合腔的回风口出口附近(图1中的灰色区域),另外四个装置呈U型均布于客室顶部的天花板结构中(如图1中标注所示)。由于上述装置较小,对于客室气流组织和风道结构沿程阻力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2.2.3 底部送风模式下不同净化技术的净化效果
图5展示出了底部送风模式下,不同净化装置开启时中游测点污染物浓度的时程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种空气净化技术均能够在既有的G2滤网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客室空气的净化效率。从图5中可以看出,静电除尘技术的空气净化效果明显优于介质阻挡放电技术。在两种净化技术均未开启时,实验全程中游测点污染物峰值浓度为344 μg/m3,在开启静电除尘装置和介质阻挡放电净化装置的实验中,中游污染物测点的峰值浓度分别降低到了243 μg/m3和292 μg/m3,相比未开启净化装置的工况,峰值浓度分别降低了29.36%和15.11%。
上述讨论中已经提及,由于在实验过程中客室空气污染物浓度会在送风方式和流场特性的综合作用下出现小幅波动。因此,为了更为准确地比较不同净化技术的净化效率,现将每次播撒时间结束后客室污染物稳定下降的过程中分为两个污染物浓度区间(80~120 μg/m3和120~160 μg/m3)并计算其在单位时间内的下降效率,结果如表5所示。
表 5 空气净化技术的净化效率Table 5. Purification efficiency of air purification techniques工况 120~160 μg·m-3 区间的
净化效率/
(μg·m–3·min–1)80~120 μg·m-3 区间的
净化效率/
(μg·m–3·min–1)工况1 7.77 16.81 工况2 11.70 19.23 工况3 31.58 68.97 工况4 6.96 16.13 工况5 8.51 21.66 工况6 29.56 70.59 从表5中可以看出,静电除尘技术对于空气的净化效率明显高于介质阻挡放电技术,在高浓度区间和低浓度区间,静电除尘技术比介质阻挡放电技术的净化效率分别高169.91%和258.66%。
2.2.4 顶部送风模式下不同净化技术的净化效果
图6展示出了顶部送风模式下不同空气净化技术的净化效果。从图中可以看出,静电除尘技术对于客室空气的净化效果同样优于介质阻挡放电技术。此结论与底部送风模式下污染物浓度的变化趋势研究一致。此外,对比图5和图6可以明显看出,无论基于本研究中所涉及的任何一类净化技术,底部送风模式下的污染物峰值浓度均会明显高于顶部送风。该结论与2.1节中得出的结论一致。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是底部送风模式下导致客室内产生了的更加强烈的上升气流,从而降低了由污染物颗粒自身重力导致的沉降效应。因此更容易造成污染物颗粒在客室中部的长时间扩散。在顶部送风模式下,基于静电除尘技术和介质阻挡放电技术的空气净化装置开启时的峰值浓度分别为230 μg/m3和228 μg/m3,相比于无净化装置开启时的净化效果分别提升了16.79%和16.06%。在此基础上,同样选用两个污染物浓度稳步下降的测试区间进行空气净化技术净化效率的评价,其结果如表5所示。从结果中可以看出,静电除尘技术相对于介质阻挡放电技术仍然具有更高的净化效率。此外,综合净化技术在顶部送风模式和底部送风模式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客室污染物浓度较高时,两种空气净化技术的净化效率也会随之提升。然而当客室污染物浓度较低时,两种空气净化技术的净化效率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下降。
3. 结 论
本文通过实车实验的方式,整理出了固态颗粒空气污染物在代表性高铁列车客室送风模式下沿客室纵向方向的典型传播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基于静电除尘技术和介质阻挡放电技术两类实时空气净化技术对客室内污染物颗粒的净化效果。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基于高速列车客室的风道结构设计,在客室内部会形成一个纵向气流,但是中下游区域产生的空气污染物仍会通过湍流对流的形式传播到上游区域。
2)在客室污染物颗粒浓度较高时,污染物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会显著增强,该不均匀性是由流场的湍流脉动随机性造成的。由于客室风道结构的设计,底部送风造成的湍流脉动和污染物浓度的时空波动相较于顶部送风更为剧烈。
3)基于现有的高速列车客室结构、风道设计和送风条件,外循环模式对PM2.5的净化效率比内循环模式高4.68%;由于底部送风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污染物由客室内垂向的下部向回风口所在的上方区域运动,从而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回风结构混合腔中滤网结构对污染物的净化效率。因此,底部送风模式对PM2.5的净化效率比顶部送风模式高5.76%。
4)介质阻挡放电技术和静电除尘技术均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客室内固态污染物颗粒的浓度。实验结果表明,在80~160 μg/m3的浓度区间内,静电除尘技术对客室污染物的净化效率比介质阻挡放电技术高60%以上。
本研究的成果在高铁客室污染物浓度实车实验和空气净化技术的工程应用方面具有先导性的借鉴意义,其结论能够为后续的高速列车客室流场空气动力学研究和高速列车客室环境友好优化设计提供理论支持。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中,建议更加全面地分析客室座位横向位置的污染物浓度扩散规律,并优化净化技术在高速列车工程应用过程中的空间布局,进一步提升空气净化技术的净化效率。
-
图 2 净化装置和客室结构布置图:(a)污染物发生装置;(b)介质阻挡放电装置代表性安装位置(图片左上方);(c)静电除尘装置安装位置(图中左侧滤网附近位置)
Figure 2. Air purification unit and passenger cabin structure: (a) air pollutants generator; (b) typical installation location of the DBD unit (upper left of the picture); (c) installation location of the IFD unit (near the filter on the left of the picture)
表 1 污染物浓度传感器性能参数
Table 1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the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sensor
检测原理 检测量程 PM2.5检测精度 数据采集频率 激光散射
原理0~1000 μg/m3 ≤100 μg/m3; ±10 μg/m3
100~1000 μg/m3; ±10%
(以GRIMN作为参考,
25±2℃,50±10%RH环境条件)1 Hz 表 2 研究工况
Table 2 Cases under investigation
工况编号 送风/空气净化技术条件 1 内循环-底风-G2滤网 2 内循环-底风-G2滤网 + DBD 3 内循环-底风-G2滤网 + IFD 4 内循环-顶风-G2滤网 5 内循环-顶风-G2滤网 + DBD 6 内循环-顶风-G2滤网 + IFD 7 外循环-底风-G2滤网 8 外循环-顶风-G2滤网 表 3 典型工况下污染物颗粒浓度峰值及达峰时刻
Table 3 Peak concentration and the time to peak of pollutant particle concentration for typical cases
送风模式 PM2.5浓度峰值/(μg·m–3) 达峰时刻/min 工况1 344 19 工况4 275 15 工况7 294 16 工况8 262 15 表 4 PM2.5浓度从160 μg/m3降低到80 μg/m3所需时间
Table 4 Time required for PM2.5 concentration to decrease from 160 μg/m3 to 80 μg/m3
工况 时间 工况1 11ʹ20ʺ 工况4 12ʹ20ʺ 工况7 11ʹ09ʺ 工况8 11ʹ27ʺ 表 5 空气净化技术的净化效率
Table 5 Purification efficiency of air purification techniques
工况 120~160 μg·m-3 区间的
净化效率/
(μg·m–3·min–1)80~120 μg·m-3 区间的
净化效率/
(μg·m–3·min–1)工况1 7.77 16.81 工况2 11.70 19.23 工况3 31.58 68.97 工况4 6.96 16.13 工况5 8.51 21.66 工况6 29.56 70.59 -
[1] ZIMMERMAN R S. Indoor air quality guidelines for Pennsylvania schools[R/OL]. 1999, 5: 2−17. https://www.docin.com/p-1641068665.html
[2] HO A F W, ZHENG H L, EARNEST A, et al. Time-stratified case crossover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 of outdoor ambient air pollution with the risk of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the context of seasonal exposure to the Southeast Asian haze problem[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2019, 8(6): e011272. DOI: 10.1161/jaha.118.011272
[3] JAYARAJ R L, RODRIGUEZ E A, WANG Y, et al. Outdoor ambient air pollution and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the neuroinflammation hypothesis[J]. Current Environmental Health Reports, 2017, 4(2): 166-179. DOI: 10.1007/s40572-017-0142-3
[4] 赵传阳, 李永安, 刘学来. 粉尘PM2.5及其对人体的危害[J]. 制冷与空调(四川), 2013, 27(4): 403-406, 419 ZHAO C Y, LI Y A, LIU X L. PM2.5 and its impact on the health hazards[J]. Refrigeration & Air Conditioning, 2013, 27(4): 403-406, 419. (in Chinese)
[5] 肖春华. 面对面呼吸飞沫传播和防护的流体力学初步分析[J]. 空气动力学学报, 2021, 39(02): 133-141 XIAO C H. Preliminary fluid dynamics analysis on face-to-face respiratory droplets transmission and protection[J]. Acta Aerodynamica Sinica, 2021, 39(02): 133-141. (in Chinese)
[6] LIU W, MAZUMDAR S, ZHANG Z, et al. State-of-the-art methods for studying air distributions in commercial airliner cabins[J].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2012, 47: 5-12. DOI: 10.1016/j.buildenv.2011.07.005
[7] MAO Y Y, WANG J, LI J M.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y of air flow and temperature variations in an electric vehicle cabin during cooling and heating[J].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 2018, 137: 356-367. DOI: 10.1016/j.applthermaleng.2018.03.099
[8] TAO Y, YANG M Z, QIAN B S, et al. 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ventilation panel models in a subway passenger compartment[J]. Engineering, 2019, 5(2): 329-336. DOI: 10.1016/j.eng.2018.12.007
[9] LIN C H, HORSTMAN R H, ABLERS M F,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airflow and airborne pathogen transport in aircraft cabins - Part II: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airborne pathogen transport[J]. Ashrae Transactions, 2005, 111(Pt1): 755-763.
[10] LI Z Y, CHE W W, FREY H C, et al. Factors affecting variability in PM2.5 exposure concentrations in a metro system[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8, 160: 20-26. DOI: 10.1016/j.envres.2017.09.006
[11] WALGAMA C, FACKRELL S, KARIMI M, et al. Passenger thermal comfort in vehicles - A review[J].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Part D: Journal of Automobile Engineering, 2006, 220(5): 543-562. DOI: 10.1243/09544070d00705
[12] MAIER J L, MARGGRAF-MICHEEL C, ZINN F, et al. Ceiling-based cabin displacement ventilation in an aircraft passenger cabin: Analysis of thermal comfort[J].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2018, 146: 29-36. DOI: 10.1016/j.buildenv.2018.09.031
[13] ELMAGHRABY H A, CHIANG Y W, ALIABADI A A. Ventilation strategies and air quality management in passenger aircraft cabins: a review of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2018, 24(2): 160-175. DOI: 10.1080/23744731.2017.1387463
[14] 翟萌, 姜惠芬. 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的传播途径及预防和防护[J]. 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 2020, 39(10): 4895-4898 ZHAI M, JIANG H F. Transmission route,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of COVID-19 caused by SARS-CoV-2[J]. Genomics and Applied Biology, 2020, 39(10): 4895-4898. (in Chinese)
[15] BORRO L, MAZZEI L, RAPONI M, et al. The role of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diffusion of Sars-CoV-2 in indoor environments: a first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 model, based on investigations performed at the Vatican State Children's hospital[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21, 193: 110343. DOI: 10.1016/j.envres.2020.110343
[16] 闫新, 杨秀琴, 张利军. 空气净化器用过滤材料透析[J]. 洁净与空调技术, 2015(4): 82-85 doi: 10.3969/j.issn.1005-3298.2015.04.022 YAN X, YANG X Q, ZHANG L J. Dialyse the filter material of air cleaner[J]. Contamination Control & Air-Conditioning Technology, 2015(4): 82-85. (in Chinese) doi: 10.3969/j.issn.1005-3298.2015.04.022
[17] 刘俊杰. 高效纤维滤料最易透过粒径计数效率的研究[D]. 天津: 天津大学, 2007. LIU J J. Study on the particle count efficiency at the most penetrating particle size for high efficiency fibrous filter media[D].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2007(in Chinese).
[18] 王晓斌, 杜雅兰, 王东黎. 重雾霾天气条件下高铁客运系统细颗粒物及净化技术调查[J]. 铁路节能环保与安全卫生, 2017, 7(2): 92-95 WANG X B, DU Y L, WANG D L. Investig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of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in high-speed railway passenger transport system[J]. Railway Energy Saving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2017, 7(2): 92-95. (in Chinese)
[19] 黄修涛. 阵列式介质阻挡放电处理空气颗粒物(PM)的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7. HUANG X T. Investigation on degradation of particulate matter (PM) by array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D].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 (in Chinese).
[20] 艾庆文. 室内静电净化装置的设计与性能研究[D]. 上海: 东华大学, 2005. AI Q W. Development of indoor air cleaner and research on its performance[D].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 2005 (in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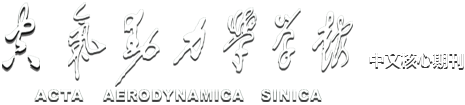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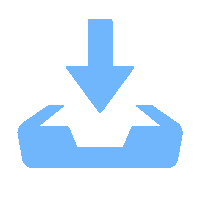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